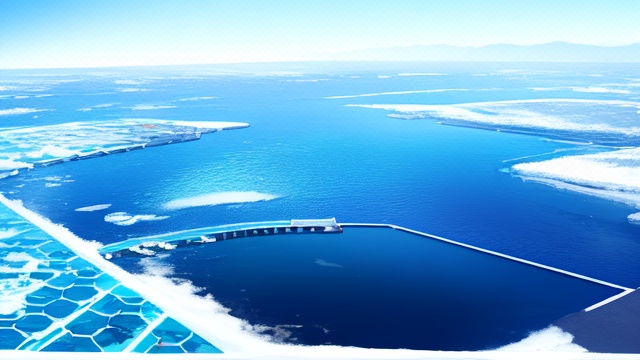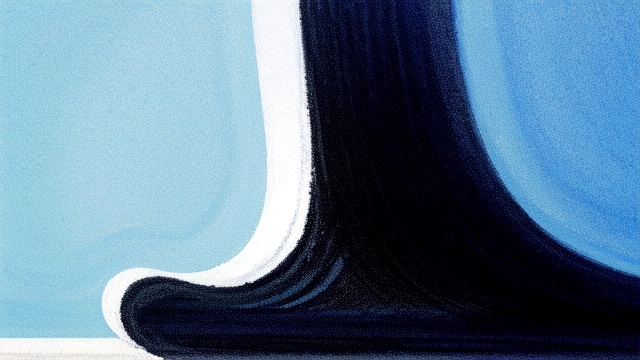涪陵礼服服装定做店在哪里-涪陵礼服服装定做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与人物

PDF版的发到你邮箱里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与人物
赵琴玉
[摘要] “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 (张爱玲语),于是,她将各
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示,这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
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也使她的小说风味迥异,绚丽多姿。
[关键词] 张爱玲;服饰;人物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人物服饰的描写是丰富
而极细致的。她曾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
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张爱铃这种对服饰的敏感贯
穿在小说创作审美和存在哲学中。 “生命是一袭华
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用服饰对生命作了
这样的隐喻或诠释。
张爱玲对衣服的敏感和妥帖表述的天赋,说明
她是一个喜爱表现、也擅长表现的女子。她论起颜
色、服饰、公寓、街景、影戏这些女人气十足的话
题,皆津津有味。巴黎的时装、伦敦的礼服与长袍
马褂混杂相陈,而她经常的穿着则是色泽淡雅的丝
质碎花旗袍,自己设计时装,穿上自己制作的艺术品
款款过市;也许是明朝的袍,配着时兴的欧式小帽,
在现在可以看到的她当年的照片中,你可以不费力
的找到各种各样的姿态,英式的、法式的。她独
特的审美注视至今都令人惊奇。从《更衣记》中,
清清楚楚的介绍满青乃至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历
程,到《童言无忌》的《穿》中道出自己对“穿”
的理想,对“穿”的诠释, “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
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
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 “再没心肝的女
子,提起去年那件锦缎长袍,还是含情脉脉的”。
内衣于女人也‘是一样,不只是对身材的呵护与保
养,那些娇嫩的颜色,动人的款式,总像一只手在
伸向你,把你的心搅得乱乱的。把内衣穿得细致而
妥贴的女子是值得去爱的,纷繁的生活总有许多不
如意的地方,但是在心中保留一份浪漫情致的女子
却可以永葆青春”, “我既不是美女,义没有什么
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别人的注意?”
文字的聪慧孕育了她直觉的敏感,她将自己的
“活色生香”与传统的东方文化完美的结合起来,不
流俗,不噱头,既有感性的叛逆,又有希望被用一种
“挑剔”的优雅,雕塑出一个个性十足,引领潮流的
张爱玲,展现着她的叛逆、优雅、落寞与欢容。
什么是所谓女性品质?作为男人的西
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
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 人的生命
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女人的献身不
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抽
象性的观念, 而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
性—— “一种时间性的、似乎一点一滴的
东西”。女人的生命直觉就在生命本身当
下的流动中,而不是像男性的生命直觉那
样置身这种流动之外。西美尔对男性品质
下了这样的判词: 男性追求的不是生命整
体,而是生命的栽体,不是灵魂本身,而
是灵魂的功能,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
的方式— — 结论是: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
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
人。“女人与男人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就自
己是女人这一点对女人来说, 比起自己是
男人这一点对男人来说,更具本质性”。
张爱玲对服装的喜欢和丰富而极细致描述来自
她女性特质下的女性视角,她不是从社会地位上,
而是从女人内含的悲剧性质上去说明,文字一寸一
寸都是女性的感觉。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又有一句: “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
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麦克卢汉在他的代
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服装一章中阐述
道:作为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之一,服装以最直
观的方式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所处的时代,他所属
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别、社会地位、财产、教养等
等的信息。
张爱玲将各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
示,对于服饰她在乎的应该是服饰的本体特性,它
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
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这使她的小说绚丽
多姿,风味迥异,也正是这点为她作品中运用人物
服饰,在修饰人物,充当人类遮羞布的同时,又赋
予新的生命,新的用途。
(一)展示身份、渲染氛围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一篇《更衣记》不仅追溯
了旗袍的演变,更赋予其时代变迁、心理变异的脉
动。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
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各人住在各人的衣
服里,各自打理。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振保无意撞见烟鹂在浴
室: “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
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
的高高的,一半压在颌下,睡裤臃肿的堆在脚面
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污秽的画
面让人不由生出厌恶之感,尴尬的气氛在她与振保
之间急剧的升腾,她与裁缝的那段大家心知肚明的
尴尬,更是讽刺的有力的爆炸开来。夫妻间的欺
骗、肮脏、虚伪在那一瞬间被赤裸裸的暴露出来,
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却正是这个单调无味的女
人。她的出场便笼罩着笼统的白,而后来连这少女
的白也变成了妇人的呆板、僵硬和空洞, “床前明
月光”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又如王娇蕊。穿“一套睡衣,是南洋华侨家常
穿的纱笼布制的袄裤,那纱笼布上印的花,黑压压
的也不知是龙蛇还是草木,牵丝攀藤,乌金里面绽
出绿”复杂的印花,滋长了娇蕊和振保之间暖昧不明
的气氛,印证了娇蕊对振保全新的、异于对待其他所
有男人的牵丝攀藤的用心的感情,这是犹如海底捞
针水蒸气一般的用肉眼所看不清的和无法明白的、:
《金锁记》曹七巧用黄金的斧无情的劈砍儿女
的幸福,对童世舫大摆鸿门宴之时,她的服饰便透
露了一种骇人的气氛。“她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段
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封建遗留的“青灰团
龙宫织段袍”与现代文明产物红色热水袋处于同一
平面,无疑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强烈的不调和的对
比在空气中弥漫出紧张、骚动、不安的气氛。生活
的空气因孟烟鹂而凝滞、苍白,又因曹七巧而慌
乱、紧张。
从服饰以及最初形态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之时,
到后来出现的锦帽貂裘,布衣之别,服饰总是理所当
然的承担了一种功用:表明人物的年龄,身份,地位。
在张的小说中,服饰依然承担起这种职责和义务,为
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体系夯实了坚实的地基。
《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说“难得碰见像你这样
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省亲之夜,单凭跳舞就搅
了七妹宝络的局。那天,她穿的是“床架上挂着她脱
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他一歪身坐在地上”,
“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无论是穿什么,都是逼
上粱山,被置于一个哪里” “有点不对” 的戏台
上。拿白流苏陪同七**去相亲时穿的月白蝉翼纱
旗袍而言,月白色透露的是内心的宁静和明晰,蝉
翼纱的面料流泻出的是内心的轻松感,她已无所谓
家人的职责和嘲讽,她有的是得胜后的从容和冷
静。轻灵的飞纱中飘逸的是她对范柳原的若有似无
的飘渺的情感,是一种连她自己也不理解的神秘莫
测、飘忽游移的心思。
人们为了渲染某种气氛,通常运用大量的色块
或通过环境描写等手段,却很少象张爱玲一样借助
服饰渲染一些特殊的氛围。
(二)刻画人物性格、心理
典型人物是优秀小说的感性底子,而不同的作
家打磨人物也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张塑
造人物的独特趋向和细致手笔尤其不容忽视。她在
小说中塑造人物、完善人物性格使,以服饰现性
格,虽有信手拈来之态,然兴味深远,蕴涵丰富,
各色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穿,流连于服饰五
彩斑斓的流光中,演绎着他们平凡的生活。
从古时的训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到今天的时装业的逐渐与国际潮流接轨,人们知道
了依时、依地、依情来配置适合的服饰,而张爱玲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他的小说中向我们展示
了一种丰富的服饰心理。
在曹七巧这个特殊女性身上,服饰心理描写更
为精妙在《金锁记》中作者写道“只看见发结上
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挚动
着,发 的心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的火阎里。那
风凉针上的钻石,正像七巧的心中凝固的泪珠,那
一小截粉红丝线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正常内心对人性
之爱热情的追求,冰冷的钻石闪闪挚动的光,是一
个悲哀女性辛酸的泪光。于是,她在不幸的生活中
将希望都寄托在小叔子姜季泽的身上。在她寡居后
听姜季泽来访时,特地系上一条玄色铁线纱裙”。
这一细节中包藏着的是他的期待和冲动。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 “她(艾许太太)是
高高的,驼驼的,穿的也是相当考究的花洋纱,却剪
的拖一片、挂一片,有点象老叫花子,小鸡蛋壳青呢
帽上插着双飞燕翅,珠头帽针,帽子底下镶着一圈灰
色的鬈发,非常像假发,眼珠也像是淡蓝瓷的假眼
珠。”如此的奇装异服,不过是她想极力的证明自己
不同于中国人的身份,维护她那个家庭的“尊
严”,然而,她这种过度夸张的装束却反而使服饰辩
白变的可笑,自暴追求英国身份的虚荣心。
写骄蕊“穿着暗紫蓝乔其纱旗袍,隐隐露出胸
口挂着的一颗冷燕的金鸡心” “一动也不动像一颗
蓝宝石,只让梦幻的灯光在宝石深处引起波动的光
和影”。暗紫蓝的旗袍庄重中有忧郁、冰冷中含诱
惑.乔其纱则以其飘逸的质地道出了女性柔美的本
质,透过这种带朦胧感的面料,人们可以窥见她内
心的飘忽虚浮的情感世界。而那颗冰冷的“金鸡
心”是静静地骄傲的散发着她高贵和不容忽视的
“冰美人” 的魅力。
《封锁》中“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
窄窄的花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质朴的味道。她
携着一把百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
样,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这是吕宗桢在电车上
见到的吴翠远。蓝和白,肃静的色彩,让人感觉到
天使般的纯洁。确实,在家里,她是个好女儿,在
赵琴玉: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与人物口 153
学校是个好学生。大学毕业在母校担任英文助教,
然而,也正是这天使的颜色使她的思想停留在书本
上,使她在安详的挑战中不自觉的倾向与幻想,他
的服饰和她的思想是再切合不过了。
《等》中的童太太“薄薄的黑发梳了个,年青
的时候想必是端丽的圆脸,现在胖了,显得脓包,
全仗脑后的“一点红” 的红宝簪子,两耳绿豆大的
翡翠耳坠,与嘴里的两颗金牙,把她的一个人四面
支柱起来,有了着落”。红金绿玉将“灰呢村衫袍
的端庄、稳重感一扫而尽,乘下的是她爆发户的虚
荣,掩饰着他被弃的怨妇情怀,寒酸和荒凉以及她
骨子里的恶俗之气。
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而形成不同的审
美情趣,导致他们在服饰上的品味迥异.因而往往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服饰中反观其地位乃至品位。
(三)暗示人物灵魂与命运
服饰是一种奇炫的东西,经人类几千奶奶的历
史长河淘洗并不断发展,服饰本体不仅是几千年的
文化沉淀,而且包含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趋于完善
的历程中对服饰的理解几服饰的人性化,因而,犹
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于
服饰,人们也各执一词。
《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她穿着一件异地长袍,
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
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
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了一寸
半的裂缝,用绿缎子十字交叉一路绿了起来,露出
里面的深粉红的裙”。这是描写红玫瑰王娇蕊的一
段,过分刺H艮的绿红色调是红玫瑰的典型色彩,工
娇蕊是朵艳丽的交际花,后来成了王太太,已经是
别人的妻子,却仍与旧情人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
系,并且还不断的挑逗佟振葆。她这种谙于男女周
旋的性格特征冲作者对其衣着的色彩描写中看出
来。作者通过把视觉、味觉、触觉糅合在一起,使
视觉效果达到了最佳,通过服饰的色彩就已经初步
展示了人物的灵魂。
《沉香屑 第一香炉》里的梁太太“一个娇小
格致的西装**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下垂下
绿色的面网,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
泪珠,暗的时候更像一粒清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
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浮浮。”梁太太的出
场,以黑色昭告天下,又像时髦,有似丧失的装扮以
及那欲坠未坠的泪珠。这一切都暗示了她本身的不
维普资讯 幸,在她的身上充满了在古来腐朽的文化,物欲,情
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十八春》曼潞, “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
穿着件淡灰色的旧洋皮大衣”, “她在户内也围着
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
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
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
的暗蓝色封面。”“穿着一件苹果绿软长旗袍,倒有
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
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衣裳上忽然现出这样一个
黑隐隐的手印,看上去却有一些恐怖的意味”
“曼潞瘦得整个的人都缩小了,但是衣服一层层得
穿得非常臃肿,倒反而显得胖大 ”从几个时段
的服饰,可以看到她的变化。
在《金》中张爱玲对七巧性格的塑造始于小说
的开始,即通过对服饰性格的打造人物轮廓, “她
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在门上——玻璃
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蝴蝶用牺牲自己
圆了一个美丽的梦,永远留下了当年的韶华;黄金的
枷锁将七巧牢牢扣住,把她抛在金钱的欲望中苦苦
挣扎,在肉体的欲望中迷惘。等到青春和自我迷失在
姜家的大宅后,她却依旧不知道能不能在上帝的伊
甸园中圆她那个飘洒着金色浮光而又凄怆的梦。此
外,对七巧的反复雕琢,除了完成其自身的服饰性格
化之外,还援引了他人的服饰加以补缀。如写她为长
安裹脚,重拾弃之已久的裹脚布,完全是由对一个男
人的温柔回忆而引起的神经质的突发兴致,是自私
而无情地对女儿健康身心的摧残,将女儿推人一个
充满陈腐之气的世界中。然而,可笑又可气的是,巨
大代价的付出却只为满足她自己极端的专横和变态
的私心。她的愿望不过是企图通过束缚长安的身体
来禁锢女儿年轻而美好的心灵和幸福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七巧的残酷和变态并非生而有
之,她的性格始终是变化着的,通过她的“翠玉、
镯子”可见一斑。年轻时翠玉镯子里的是一条滚圆
的手臂,有着青春的朝气,健康的活力,年老时,
翠玉镯子里的是一条干巴巴的裹着一层毫无弹性的
皮肤的手臂, “可以一直将镯子到腋下”,这是七
巧青春的消逝所伴随的生命力和人性的弱化,是饱
受煎熬的生命迷失自我、迷失本性后遗留的残渣,
是一个残酷破坏儿女幸福的自私、疯狂、变态的母
口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亲,是因一生算计和提防以至熬干血肉的干涸的幽
灵,是来自人间地狱的罪恶的魂灵。
张爱玲曾在《穿》中说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
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
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在对王娇蕊服饰的
描写中便有这样的痕迹:“她穿着一件一地长袍.是
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似乎
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
交叉一路路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显
然,这是受了张恨水的影响。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
渗透力、感染力,蕴涵着活泼的、生命律动的意味,衍
射出“红玫瑰”的鲜辣、活泼的个性色彩,而分红色
的衬裙则犹如激情背后的温柔,体贴、细腻而妩媚,
是深锁于记忆中的一段粉红的回忆。
当然,服饰是一片施展个性的天地,不管是表
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
是渲染气氛,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最终的还是那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因为一篇小说常常是必须建立在
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的基础上的。在这,张既施展了
她的个性,也将这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或
许着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衰隋与服饰文化的原因之
一吧。张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
有些重叠。仿佛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
自己变质一件衣裳,汇成了她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有评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思想经历都能映在画面上,仅此一点,他的人格
就会凹凸出来,而且清晰明朗,他的状态就是一种
精神。用衣服来演示女性的生命,展示的是各色人
物的百般滋味的平凡人生.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生存
状态。因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
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
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